- 翰林提供學術(shù)活動、國際課程、科研項目一站式留學背景提升服務!
- 400 888 0080
我從平和步入哥大!英美文學帶給我的審美享受和存在性焦慮…
#1
寫在前面
讀者您好。
現(xiàn)在您眼前所見的這些文字,是我第三次新建空白文檔,寫下的第三個開頭。
在這樣矛盾心理的作用下,我的前兩稿文章不盡人意:風格混雜,內(nèi)容過多,在敘述和論證之間搖擺不定,在幽默和嚴肅之間來回跳躍。這讓我想到了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中,大臣Polonius給Hamlet介紹宮廷來訪劇團的一段臺詞(來自劇本的第二幕,第二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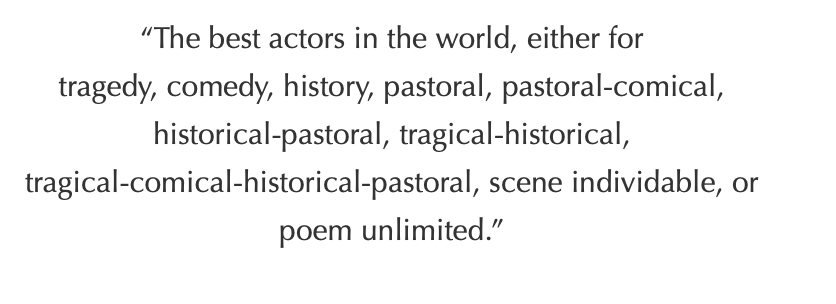
我的文章似乎也變成了一個tragical-comical-historical-pastoral(“歷史田園悲喜劇”)的“四不像”。
因此,在進行了取舍后,我決定聚焦于英美文學——我將要在大學攻讀的專業(yè)——在最近幾年給我?guī)淼闹T多反思、感悟和改變。這篇文章不是關(guān)于“專業(yè)探索”,也不是關(guān)于“熱愛如何幫助我申請上好學校”。我只想談談,作為一個母語為中文的讀者,閱讀英語文學、走進西方經(jīng)典的私人體驗,跟大家說說心里話。讓學弟學妹們了解學習的終點不是申請,而找到熱愛——你愿意為之持續(xù)付出時間和精力的東西——讓自己時常有一種overwhelming的快樂和堅定的內(nèi)心。這時,校內(nèi)成績/標化考試/申請/親子關(guān)系,一切你所煩惱焦躁的事情都變得不那么難以面對了。
#2
英美文學帶給我的審美享受
“文學有什么用?”
每當身邊的人知道了我的專業(yè)方向,隨后向我問出這個問題時(相信我,我被問到過很多次),他們總是會使用一種禮貌的語氣——聲音里夾雜一種純粹的好奇,一絲略帶歉意的無知——像是生怕冒犯到我;而我總是會用一句“嗯,這是個非常深奧的問題”來敷衍了事,略帶幽默地結(jié)束話題。
提問者們往往有著不同的意圖,而很大一部分,在我看來,實際上問的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學文學專業(yè)的學生,將來能做什么職業(yè)?有前途嗎?”不同于商科、經(jīng)濟、計算機科學,文學似乎無法匹配到一個單一的、在當今社會能有所謂“很好發(fā)展”的職業(yè)領域,因此“沒用”二字出現(xiàn)在許多人的腦海里是個非常自然的、直覺性的反應。
但這個問題不難回答,我有一個精心打磨、屢試不爽的答案:“哈哈!事實上,English專業(yè)的學生,在各個領域都可以有很好的發(fā)展,比如新聞工作、電影/戲劇工作等等,并不是所有畢業(yè)生都成為了作家或文學評論家。就我個人而言,我也很樂意將來從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把我對語言文字和經(jīng)典文學的熱愛傳播給更多人。更何況,還有很多時間去給我嘗試呢!”
這些都是實話,且能滿足大部分提問者。但我知道,這并沒有解答“文學有什么用?”的根本問題,只不過解決了“學文學之后能干什么”。從幼兒園時期閱讀兒童漫畫,一直到如今閱讀莎士比亞和彌爾頓,作為一輩子的讀者,這個問題直到最近幾年才引起我的困惑。因為很長時間以來,答案是不言自明的:閱讀文學作品當然是為了學習——學習書中的“道理”,書中的“智慧”,本質(zhì)上和數(shù)學課學習三角形的運算,生物課學習DNA結(jié)構(gòu)沒有區(qū)別。從小學到初中,當每篇課文,每個文本都能輕而易舉地被提煉出“中心思想”,一個應當在考試中被寫進答卷的標準答案,你很難不去認為,閱讀文學作品就是為了尋找這些“思想”。
然而,隨著我近幾年接觸到更多西方文學經(jīng)典,為自己的英美文學學習作準備,我發(fā)現(xiàn)提煉“思想”或“道理”成為了越發(fā)困難的一件事。倘若你問我,我最喜歡的文學作品——比如莎士比亞的《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喬伊斯的《都柏林人》(Dubliners)、福克納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教會了我什么道理,我會啞口無言,瞬間語塞。我或許會回答你,它們所涉及到的主題(藝術(shù)、戰(zhàn)爭、愛、歷史、文化),或是作者可能在進行的一些討論(比如《科利奧蘭納斯》對羅馬共和國政體的反思),但我無法告訴你它們的“道理”;或者說,我不愿去做這樣武斷的歸納。從這些龐大、復雜、豐富的文本中“提取”出一條明確的有關(guān)價值判斷的論斷(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或是作者在歌頌什么,批判什么)并非不可能或完全沒有價值,但這樣的歸納往往會抹去偉大藝術(shù)作品中常有的模糊性。
這也就是為什么,每當回想起初中語文課本對《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的總結(jié)(“歌頌仁愛、友誼和愛情,塑造了夏洛克這一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高利貸者的典型形象。”),我總會無奈地嘆一口氣。夏洛克作為一個復雜多面、有血有肉,值得同情的個體,在這樣簡單總結(jié)出的“中心思想”里蕩然無存。而《威尼斯商人》作為莎士比亞“問題劇”(problem play)的內(nèi)在矛盾和復雜點,全都被忽視了。
《威尼斯商人》里的反猶主義呢?這部劇本身是反猶的,還是說只是探討了反猶的社會現(xiàn)象?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觀眾會如何對夏洛克這個人物做出反應?《商人》如何回應了克里斯托弗·馬洛的《馬耳他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莎士比亞自己有種族偏見嗎?在解讀他的作品時,莎士比亞的私人立場真的重要嗎?我不認為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任何人能為這部莎劇總結(jié)“道理”。所以,我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文學學習中,提出問題或許比尋找答案更有價值。
但就我個人而言,更重要的是這些“道理”似乎不是我作為讀者在文學作品里最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很明確自己喜歡《哈姆雷特》或《白鯨記》(Moby-Dick)的原因不是因為它們“教會”了我什么。我不以作者為老師,更不以作者筆下的人物為榜樣。
回想我所讀過的經(jīng)典作品中,最震撼到我那些人物:喬叟《坎特貝雷故事集》中的巴斯夫人(The Wife of Bath)、荷馬《奧德賽》中的奧德修斯(Odysseus)、彌爾頓《失樂園》中的撒旦(Satan)、喬伊斯《尤利西斯》中的布魯姆(Leopold Bloom)、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的斯萬(Charles Swann),以及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麥克白(Macbeth)、理查二世(Richard II)、《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Falstaff)——他們沒有一個人是我的榜樣(我可不愿變得像哈姆雷特那么憂郁,像理查二世那么傲嬌,像福斯塔夫那么...胖?)。
但這絲毫不妨礙我在美學層面上崇拜他們、在感情層面上同情他們、在理性層面上分析他們、在私人層面上了解他們——甚至超過現(xiàn)實生活中我對朋友們的了解(每一個讀過《尤利西斯》的讀者,肯定比了解自己的好朋友更了解布魯姆)。通過閱讀,我在和這些鮮活、立體的人物進行對話、建立關(guān)系,而這個對話本身帶給我的就是一種內(nèi)在自我的擴大和成長。我不需要從中學到什么。這個過程不屬于任何功利主義的評判體系,因此也無關(guān)“有用”或“無用”。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那我到底為什么喜歡這些作品呢?不是因為它們有道理有智慧,不是因為它們是榜樣,也不是因為它們有用。奧斯卡·王爾德在給一位名為Bernulf Clegg的牛津大學學生的書信中曾寫到這么一段話——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我自己對閱讀的理解:
“Art is useless because its aim is simply to create a mood. It is not meant to instruct or influence action in any way. It is superbly sterile, and the note of its pleasure is sterility.”
王爾德,以及他所強烈支持的唯美主義思想(aestheticism),提倡“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art for art’s sake)。在他看來,藝術(shù)作品是完全非功利的,它的內(nèi)在價值不在于它的社會或政治屬性。藝術(shù)不能幫助我們改變生活,不能“教我們做事”,更不能讓我們成為更好的公民。它的價值僅僅就是“創(chuàng)造一種氛圍”罷了。
盡管我不認同非常極端的唯美主義——文學終究無法脫離歷史、社會和政治,文學也蘊含著反映社會與政治的能力——但作為讀者,我喜歡這些書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們純粹的美學價值,也就是王爾德所說的“氛圍”或情緒的營造。文學不就是(以一種其他藝術(shù)形式都做不到的方式)去捕捉情感,隨后將其轉(zhuǎn)化為語言文字,從而分享給所有人嗎?而我們,作為讀者,不就是去調(diào)動自己的感官,去體驗這些情緒嗎?理性的分析當然是必要的,但樂趣的最大來源是感性的體驗。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在小說《微暗的火》(Pale Fire)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深得我心: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Shakespeare at college level having been introduced: "First of all, dismiss ideas, and social background, and train the freshman to shiver, to get drunk on the poetry of Hamlet or Lear, to read with his spine and not with his skull." Kinbote: "You appreciate particularly the purple passages?" Shade: "Yes, my dear Charles, I roll upon them as a grateful mongrel on a spot of turf fouled by a Great Dane.”
怎么學莎士比亞?把別的都忘了,首先“get drunk on the poetry of Hamlet or Lear”——讓莎翁把你灌醉了再說。先用你的脊椎去“讀”,再用你的大腦去讀。的確如此!當代最著名(也是最有爭議)的文學評論家之一,來自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教授,作為王爾德的堅決擁護者,同樣強調(diào)“美學價值”(aesthetic merit)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提倡文學閱讀回歸最純粹的美學體驗。在美國學術(shù)界近幾十年的發(fā)展中,政治因素在越來越頻繁地影響著文學學習與研究。布魯姆教授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視作一個即將消亡的傳統(tǒng)的捍衛(wèi)者,打著一場似乎終將失敗的戰(zhàn)役。但是,正如布魯姆教授在許多采訪中所說,就算歷史和文化發(fā)展的趨勢不可逆轉(zhuǎn),從個人讀者的層面來看,對經(jīng)典文學作品的美學欣賞是不會消失的。
在1994年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中,布魯姆是這么闡釋文學閱讀的意義的:
“The true use of Shakespeare or of Cervantes, of Homer or of Dante, of Chaucer or of Rabelais, is to augment one's own growing inner self. Reading deeply in the Canon will not make one a better or a worse person, a more useful or more harmful citizen. The mind's dialogue with itself is not primarily a social reality. All that the Western Canon can bring one is the proper use of one's own solitude, that solitude whose final form is one's confrontation with one's own mortality.”
我不同意布魯姆教授的許多觀點,但他提醒了我要去成為怎樣的讀者,也提醒了我閱讀偉大文學作品的本質(zhì):這是一個調(diào)動所有感官去體驗其他世界的過程,一個代入所有情緒去認識其他人的過程,一個投入所有注意力去捕捉某種氛圍的過程,一個擴大內(nèi)在自我的過程,一個私人享受的過程(“The mind’s dialogue with itself is not primarily a social reality”)。在這個過程中,我會學習歷史,了解哲思,審視社會,洞察人性。
但最終的最終,學到的任何“知識”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閱讀時帶來的“difficult pleasure”本身。多次,當我在閱讀莎士比亞、普魯斯特、納博科夫等作家的文字時,我會突然從椅子上蹦起來,激動地指著幾行字,興奮到半天說不出一句話。在這些時候,我會感覺自己短暫地觸碰到了所謂的“崇高”,體驗到了最純粹的美學意義上的快感。這是一種仿佛心臟上壓了巨石,近乎窒息的感覺。這是一種仿佛千萬只蝴蝶同時展翅,在腦海中如煙花般綻放的感覺。也正是在這些時候,一切關(guān)于有用和有害,關(guān)于“道理”和“智慧”的考慮轉(zhuǎn)瞬即逝,我只想延續(xù)這種快樂——這種在其他任何藝術(shù)形式中我都從未發(fā)掘的快樂——并永遠沉浸于其中。
這種感覺,就像是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小說《發(fā)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中,主人公Alex躺在床上,聽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感覺。伯吉斯繼承喬伊斯的筆法,用瘋狂的語言創(chuàng)新和嫻熟的通感手法描述了聆聽音樂時的全身心享受:
“Oh it was gorgeousness and gorgeosity made flesh. The trombones crunched redgold under my bed, and behind my gulliver the trumpets three-wise silverflamed, and there by the door the timps rolling through my guts and out again crunched like candy thunder. Oh, it was wonder of wonders. And then, a bird of like rarest spun heavenmetal, or like silvery wine flowing in a spaceship, gravity all nonsense now, came the violin solo above all the other strings, and those strings were like a cage of silk round my bed. Then flute and oboe bored, like worms of like platinum, into the thick thick toffee gold and silver. I was in such bliss, my brothers.”
或許有點“meta”的是,我在讀這段文字時,我也感受到了“wonder of wonders”;穿透Alex靈魂的是貝多芬的音樂,蔓延我全身上下每個細胞的是伯吉斯完美的prose。
#3
與時間對抗
英美文學帶給我的不全是享受,還有一種折磨人的、對時間流逝的敏銳感知。
我從小學開始閱讀英語原版書籍,初中七、八年級開始接觸莎士比亞——英文閱讀對我來說一直是很平常、很有樂趣的一件事。但在十年級確定以英語為申請專業(yè)后,我心中產(chǎn)生了一種恐慌和緊迫感。我突然意識到:自己讀過的英文原著還太少、自己的英文語言能力也不夠好(對于讀文字上有難度的文學作品來說),以及將要和自己競爭的大多是英文為母語的文學愛好者們。畢竟,中國留學生群體內(nèi),有多少人申請這個專業(yè)呢?
這種恐慌感轉(zhuǎn)化成了一種對于時間的強烈感知,似乎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源自于“時間太少”。的確,在高中繁忙的學業(yè)壓力下,每天擠出時間靜心閱讀,似乎是格外困難的一件事。在這個信息爆炸的快節(jié)奏時代,太多事物——社交媒體、短視頻、游戲——可以提供即時滿足感,時時刻刻爭奪著人們的注意力。有一次有朋友問我:“怎么才能做到長時間把注意力集中在書上,克制住自己不看手機?”我回答:“這是做不到的。”唯有把手機關(guān)機,放在另一個房間里,確保自己接觸不到,才能維持較長的“無屏幕時間”。這是當下人類的“通病”,和自控力無關(guān)。最近我看了《紐約客》雜志的一篇新文章,標題是“The End of the English Major”(英語專業(yè)的終結(jié),非常震撼人心的標題哈!)。
這篇文章的作者采訪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文學教授,世界頂尖的莎士比亞學者James Shapiro(在幾個月前,我也有幸和Shapiro教授通過郵件交流了關(guān)于莎劇《科利奧蘭納斯》的問題,接下來就是校內(nèi)見了);Shapiro教授表示,自己在20年之前能夠一個月讀五本小說,如今一個月能讀一本已經(jīng)算很多了,因為太多時間都花在了網(wǎng)站、視頻、播客上。科技的發(fā)展不可避免地增加了閱讀的難度。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文章中提到,讓學生閱讀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簡直難如登天——我自己也沒能讀完Middlemarch,在差不多第兩百頁的位置放棄了。
但認識到問題的普遍性,并不能消除我的恐慌感。這種“我來不及看這么多書”的閱讀焦慮在兩個場合下最為明顯。
一是在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腦海中回想著自己一天做的事情,尤其是自己一天讀的內(nèi)容,很快就會陷入到“如果我一天讀這么多,那一個月能讀xx本書,一年能讀xx本書,一輩子能讀xx本書”的計算中。算出的結(jié)果,永遠令人失望。這句話可能從一個十八歲,邁向十九歲的人類個體口中說出有些奇怪:但每天晚上到這個時候,我很強烈地感覺到時間在從我的身體里流走。
二是在圖書館和書店。在過去的2022年,我最常去的是福州路的外文書店。看到滿書架的書,激動和恐慌、興奮和焦慮,幾乎是同時涌上心頭。那種想要馬上沉浸在書海中的喜悅,總是伴隨著“我能讀xx本書”的計算。一旦陷入了這個害人的計算過程,我就會意識到自己一輩子能看的量,不過是我眼前的這兩個小書架——我視野中的這個小角落。隨后,我會把這兩三個書架的寬度想象成我人生的寬度。沒錯,我會失望地對自己說,就這么點。這時,自己的生命無比渺小、無比短暫的殘酷事實仿佛寫在了眼前每本書的封面上,它們盯著我,嘲笑我。
因此,正是對英美文學的熱愛,讓我第一次意識到了人生的長度,時間的短暫。從左邊書架到右邊書架,不過是60年、70年(運氣好的話)的一條路。而我正在這條路上飛速行駛。我最近讀完了納博科夫的回憶錄《說吧,記憶》(Speak, Memory),這本書的開頭把人生比作“兩個永恒的黑暗之間瞬息即逝的一線光明”,而這個光明的縫隙和前后兩片黑暗比起來,實在太過渺小:
“The cradle rocks above an abyss, and common sense tells us that our existence is but a brief crack of light between two eternities of darkness.”
納博科夫的用詞“a brief crack of light”讓人立馬回想起《麥克白》中“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的獨白,其中莎士比亞把人生比作“brief candle”。這是我最早會背誦的一段莎劇獨白,也是我認為書寫人生的荒誕、短暫與無意義的最好段落之一:
“Tomorrow and tomorrow and tomorrow
Creeps in this petty pace from day to day
To the last syllable of recorded time,
And all our yesterdays have lighted fools
The way to dusty death. Out, out, brief candle!
Life’s but a walking shadow, a poor player
That 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時間與死亡是文學中最重要的母題之一,我能感同身受的文字太多,就不一一列舉了。但最有意思的是,這些文學作品還帶給了我一種和“時間焦慮”截然相反的體驗:文學幫我意識到了自己所擁有的時間之少,卻又給予了我打破這些時間的可能性。通過文學作品的閱讀,我的精神世界不僅限于當下,而是蔓延于整個人類思想的歷史長河中。當我閱讀古希臘的戲劇家們,比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我仿佛就生活在雅典;
閱讀王爾德和Saki等作家時,我仿佛就生活在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中上層社會;閱讀莎士比亞時,我存在于太多地方:古希臘(《仲夏夜之夢》)、古羅馬(《尤里烏斯·凱撒》、《科利奧蘭納斯》)、英格蘭(每一部莎翁歷史劇)、蘇格蘭(《麥克白》)、丹麥(《哈姆雷特》)、意大利(《羅密歐與朱麗葉》)、西班牙(《愛的徒勞》)。盡管自己的肉體存在是固定于當下這一個空間的,文學讓我的精神存在能夠穿梭于時空,去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建立永久的關(guān)系,擺脫現(xiàn)實生活中飄忽不定的關(guān)系和情感。
在我的個人經(jīng)歷中,最能夠證明這一點的例子是去年一段時間里,我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心情是被痛苦、失望,以及孤獨所定義的。困在自己的狹小空間里,被海量信息淹沒。從信息過載帶來的不知所措,到努力掙扎后的身心麻木,離開學校,開始網(wǎng)課頭兩天的新鮮感很快就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迅速堆積的負面情緒。但正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文學幫我打破了自身所處的時空,讓我的精神世界可以逃離令人失望的現(xiàn)實世界。
在這三個月里,我閱讀了20世紀現(xiàn)代主義最偉大的小說家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的作品。我讀完了他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Dubliners)、半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shù)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以及被許多人稱作“天書”的小說巨作《尤利西斯》(Ulysses)。在三百多頁的導讀本(Patrick Hastings老師的Guide to Ulysses)和六百多頁的注釋本(Don Gifford的Ulysses Annotated)的幫助下,我讓自己完全地沉浸于《尤利西斯》的世界中。在去年年終閱讀總結(jié)的朋友圈中,我寫了這么一句:2022年,身在上海,但心從未離開過愛爾蘭。
因此,請允許我再次引用哈羅德·布魯姆教授,在《如何讀,為什么讀》(How to Read and Why)中的這句非常正確的話:
“We read not only because we cannot know enough people, but because friendship is so vulnerable, so likely to diminish or disappear, overcome by space, time, imperfect sympathies and all the sorrows of familial and passional life.”
不同于現(xiàn)實生活,閱讀所建立的“friendship”和“sympathies”是頑強的,是“完美的”,是不會隨著時空的轉(zhuǎn)變而減弱的。
簡而言之,在與時間的糾葛中,英語文學經(jīng)典給我的感覺是雙重的、矛盾的:這些書既讓我感知到了時間的飛逝,又為我暫停時間,品嘗永恒。
#4
這里就是我的疆域
最后,我想聊一下本文的標題:“Here is my space”。這四個詞出自莎士比亞的悲劇《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的第一幕,第一場,是古羅馬后三頭聯(lián)盟中的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對自己的戀人埃及艷后克里奧佩特拉所說的。完整的臺詞如下:
“Let Rome in Tiber melt and the wide arch
Of the ranged empire fall. Here is my space.
Kingdoms are clay. Our dungy earth alike
Feeds beast as man. The nobleness of life
Is to do thus; when such a mutual pair
And such a twain can do ’t, in which I bind,
On pain of punishment, the world to weet
We stand up peerless.”
在英美文學中,從莎士比亞的臺詞里截取幾個字作為自己作品的標題,是最常見、最“老套”的行為之一。最有名的例子有:福克納的《喧囂與躁動》(The Sound and the Fury,書名出自《麥克白》);大衛(wèi)·福斯特·華萊士的后現(xiàn)代小說巨作《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出自《哈姆雷特》);當然,還有前文中提及的《微暗的火》(Pale Fire,出自冷門莎劇《雅典的泰門》)。我也來致敬一下這個傳統(tǒng),截取莎翁的這幾個詞(似乎還沒被任何有名的作家用過?),作為本文的標題。當然,這句話不是隨機選的。安東尼的這句臺詞承載了我的一段回憶、一絲自我懷疑,以及一份相應的心理安慰。
首先,說說這個回憶:《安東尼和克里奧佩特拉》是我在現(xiàn)場看過的第一部莎劇,也算是我對莎士比亞的熱愛的起源。2017年暑假,我參加了一個莎士比亞戲劇夏令營,和英國當?shù)氐囊恍┏踔小⒏咧猩黄鸨硌萘恕读_密歐與朱麗葉》。作為對夏令營課程的補充,老師們當時帶我們前往了莎士比亞的故居斯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觀看了皇家莎士比亞劇團(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當時上演的《安東尼和克里奧佩特拉》。
在觀看表演前,我并沒有讀過這部劇(事實上,我當時沒有完整地讀過任何一部莎劇。我們表演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也是刪減版的劇本。回國之后,讀了未刪減版,才品味到莎翁原汁原味的詼諧),因此在觀看過程中,大部分臺詞都是聽不太懂的,只能根據(jù)舞臺布景、人物動作,以及臺詞里的關(guān)鍵詞,對劇情進行很基本的推斷。但也正是在這個“聽不太懂”的情況下,我被舞臺上發(fā)生的一切深深吸引。
莎翁的語言如海浪般撲打在我身上,充滿韻律與魔力。搭配上金碧輝煌的舞臺布景(畢竟是埃及艷后的宮殿)和演員們充滿力量的臺詞表演,莎士比亞的每一個詞都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記——哪怕我當時不完全知道它們的含義。也就是在那次表演(以及幾天后在倫敦的The Globe Theatre觀看的《第十二夜》)之后,我心里栽培一下了一顆熱愛莎劇、熱愛英語文學的種子。
選這句的第二個原因是,很長時間以來,我心中總有著一絲自我懷疑:總覺得英語文學是一個不屬于自己的領域,沒有中國留學生會學這個的。作為非母語者,語言的隔閡消除后,似乎還有一重文化的隔閡。就算事實是我的英文閱讀能力已經(jīng)超越了大多數(shù)同齡的英文母語者,就算我已經(jīng)鉆研了大多母語者一輩子都沒有接觸過的經(jīng)典文本(曾聽過一句玩笑話,“經(jīng)典”的定義就是大部分人都沒讀過,但都希望自己讀過的書),就算在討論某些學術(shù)話題時,我甚至覺得自己的英語用起來比中文更流利,但內(nèi)心無法安靜下來的一個聲音是:我不屬于這里——就像安東尼拋棄了羅馬,不顧國事,來到埃及尋歡作樂一樣。脫離語境,“Here is my space”看上去像是一句莊嚴的宣告,實際上只是安東尼熱戀之中說出的情話罷了。
我也逐漸認識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并不妨礙我對另一個語言、另一個文化中的文學作品(或任何的藝術(shù)作品)有著癡迷般的熱愛。每次想到這里,我總會舉兩個例子提醒自己: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英美文學史上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他最有名的那些作品,比如《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都是用英文寫的。
然而,他的母語是波蘭語,一直到20多歲英文還說不流利。還有本文已提到數(shù)次的納博科夫——他的母語是俄語,但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把英語拆解、重組,像魔術(shù)師一樣把英語文字玩弄于股掌之間。我并不是說,我這輩子(或任何一輩子)能成為像納博科夫或康拉德這樣的作家。只是說,在非母語中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學習做到巔峰造極,是完全有可能的。語言不是障礙。沒有什么是我應當考慮的障礙。只要我現(xiàn)在喜歡它——就像安東尼喜歡埃及艷后那樣——那這里就是我的疆域。
感謝父母從小到大給予我的關(guān)愛、鼓勵和支持;感謝在我探索自身熱愛的道路上遇見的朋友們;感謝每一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感謝文學、戲劇,還有藝術(shù)本身。是你們讓我成為了今天的自己。

最新發(fā)布
?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滬ICP備2023009024號-1









